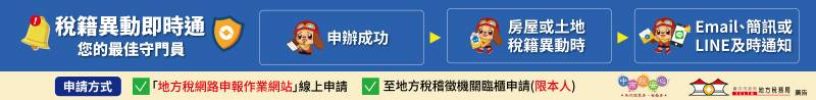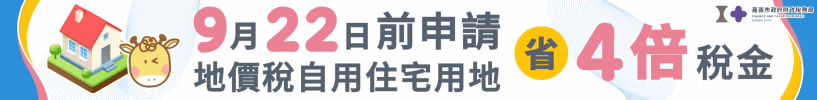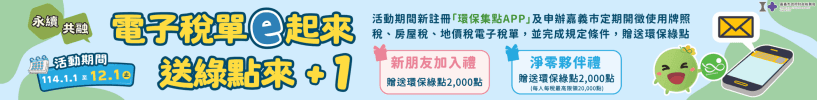(焦點時報/鄒志中報導) 投資「回流」臺灣的真相?自2018年美中貿易戰引發全球供應鏈加速重組以來,臺灣政府順勢推出了「投資臺灣三大方案」(臺商回臺投資、根留臺灣企業、中小企業投資方案),旨在引導臺商資金回流、推動產業升級,並作為穩定國內投資與創造就業的關鍵策略。
五年過去,行政部門宣布的成果光鮮亮眼:總投資金額已突破新臺幣2.5兆元,創造了超過16萬個本國工作機會,這數字在國際動盪中,似乎堅定地確立了臺灣經濟的韌性。然而,監察院近期發布的調查報告,卻揭示了執行面中存在的諸多的矛盾與結構性的缺陷,迫使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這些巨額投資究竟是驅動產業升級的有效引擎,抑或只是一種「以政策補貼堆砌出的統計成就」?
這不僅是單純的行政效率問題,更深層次地指向了政策方向能否真正回應臺灣產業長期積弱的核心困境。如果我們僅僅追求「亮眼的投資總額」,卻未能有效提升產業的實質競爭力,那麼短期內的繁榮景象,在長期來看可能反倒成為拖累國家發展的財政與產業包袱。

形式合規與實質空洞的落差
政府對投資延遲的解釋,多以「投資期程需3至5年」為由。然而,監察院揭露的核心問題並非單純的進度延宕,而是「投資承諾」與「實際產能或升級要求」之間的實質落差。
報告指出,有部分申請廠商以租賃未登記工廠作為投資地點,這反映出政策制度設計對於產業運作的真實性要求鬆散。此外,部分廠商在貸款比例及資金流向上的疑義也受到質疑。雖然經濟部回應這些案件皆「符合不超過投資成本80%」的規範,但癥結點不在於是否「合乎規範」(Compliance),而在於政策設計是否真正「有效」(Efficacy)。
換言之,三大方案存在極高風險落入「形式合格、實質空洞」的困境:企業依循程序借了錢、租了地、甚至蓋了廠,但承諾的技術升級、高價值產能,乃至於關鍵研發投資,卻未必真正發生。這使得政府投入的大量資源,可能只是被用於企業的財務周轉或既有產能的輕微擴張,而非結構性的創新與升級。

中小企業的困境與就業品質的考驗
政策在針對中小企業的行動方案中,其結構性問題尤為顯著。中小企業是臺灣經濟的骨幹,但同時也普遍面臨資本不足、技術更新緩慢、人才流動性高及接班困難等長期挑戰。
如果政策提供的僅是資金補助,缺乏系統性、針對性的輔導機制來提升技術研發、人力素質和全球行銷能力,那麼這些補助款無異於一種「止痛劑」。它只能暫時延緩產業惡化,卻無法根治產業體質虛弱的病灶。
其次,關於創造逾16萬個本國就業機會的宣示,我們必須審慎探討:這些新增的工作機會,是否屬於高價值、高薪資的職位?
如果新增職位多集中於低階製造業的生產線、基礎倉儲物流,或需大量仰賴移工補充的基礎人力,那麼我們所觀察到的不過是「就業總量」的增加,而非「就業品質」的提升,更未能解決長期困擾臺灣的技術人才斷層問題。
監察院建議「廠商應與員工共享投資成果」,並非無的放矢,而是直指臺灣社會長期低薪、青年高學歷低薪、企業獲利分配不均…等的核心矛盾。若「投資回流」的結果只是少數企業資本利得大幅增加,而廣大員工的實質所得改善有限,那麼政策的受益者將是少數資本持有者,而非整體社會結構。
這讓人不禁反思:三大方案的政策目標究竟是在改善產業結構,還是在替企業降低風險、提高利潤?

走向戰略產業,避免補貼依賴的惡性循環
政府最新宣布,三大方案將延長至2027年,並擴大適用對象至全球臺商及外商,政策焦點同時鎖定「五大信賴產業」與「六大核心戰略產業」。這標誌著政策從單純鼓勵「資金回流」,轉向更具目的性的「供應鏈韌性與技術戰略」建設。
然而,當政策走向以戰略產業為導向時,最大的挑戰隨之而來:臺灣究竟應當以何種方式在全球市場中取得優勢?
如果僅將「補貼」作為吸引投資或扶持戰略產業的主要誘因,臺灣恐將陷入「補貼依賴」的惡性循環。長期而言,這不僅無法有效提升全球競爭力,反而會嚴重削弱財政空間,擠壓政府在教育、基礎科研與公共建設等關鍵領域的長期投入。
歷史經驗一再證明:長期依賴保護與補貼的產業,往往難以淬鍊出真正的技術實力與市場敏銳度。只有主動接受市場競爭壓力、持續投入技術創新與人才培育,才能真正形成可持續、難以取代的競爭優勢。
追求「留下的能力」,而非「回流的資金」
因此,我們對三大方案的最終評估,不能單單聚焦於「投資金額是否夠大」或「廠商數量是否增長」,而必須回歸到最根本的三大指標:
- 結構升級: 這些投資是否真正讓臺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向上提升,從代工製造轉向高附加價值的創新中心?
- 社會公平: 這些投資是否有效改善長期低薪、技術斷層與人才外移的結構性問題?
- 成果分享: 經濟成長的果實是否公平地分配給廣大人民,而非僅集中於企業的資本獲利?
如果答案不明朗,那麼政策成效就不能以冰冷的數字為唯一指標,必須回到「產業競爭力」與「社會分配公平」的根本原則進行評估。
臺灣的未來,不能只追求短暫「回流的資金」,而必須以建立長期、可持續的「留下的技術」為核心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