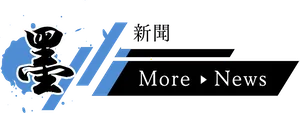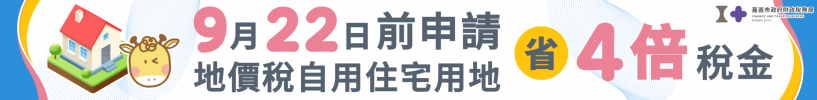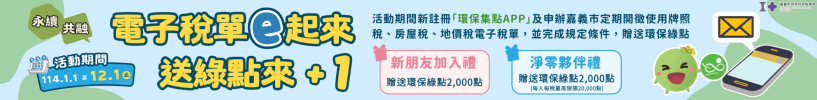(焦點時報/鄒志中報導) 賴清德總統近日接連拋出兩段引發爭議的說法。一方面,他在公開談話中回應外界批評,語帶不滿地反問「抓包我自創憲法」;另一方面,面對立法院尚未完成明年度總預算審查,卻又強調「憲法規定今年底一定要審完」,彷彿憲法的程序問題只要他一句話就能解決?這兩段談話乍看之下各自獨立,實際上卻共同指向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總統開始以政治語言重新詮釋憲法,台灣憲政的邊界是否正在被悄悄改寫?
憲法原本是用來限制權力的工具,而不是政治人物用來辯護自身立場的修辭資源。當「憲法怎麼說」變成「我怎麼說憲法」,那麼制度的重心就已經從法治轉向個人詮釋,這正是民主政治最需要警惕的時刻。
先從「今年底一定要審完預算」這句話談起。依據《憲法》與相關法律設計,立法院確實負有審議年度總預算的責任,但憲法從未規定必須在某一個確切日期前完成,更沒有授權行政部門以此作為政治施壓的工具。立法院預算審查的本質上是立法權對行政權的制衡機制,容許質詢、刪減與凍結,本來就是《憲法》制度設計的一部分。若僅因為行政部門希望快速通過,就將「程序審查」標籤為「違憲拖延」?這種說法的本身,才是真正對憲政精神的嚴重誤解。

問題不在於立法院預算該不該審完,而在於總統是否有權用模糊的憲法語言,對立法院施加「政治壓力」。當行政權開始以「憲法」之名強迫要求立法權要完全配合時,「三權分立」就不再是制度,就只剩「口號治國」?
另一段「抓包我自創憲法」的回應,則更值得細究。這句話表面上是情緒性的反擊,實際上卻暴露出一種危險的心態:把對憲政論述的質疑,視為「政治攻擊」,而不是制度的討論。民主國家的總統,本就應該接受最嚴格的憲法檢視,因為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政策方向,都可能對政治制度產生實質影響。當總統選擇用「反諷」與「嘲諷」來回應憲法爭議,等同於就是把「公共理性」降格為「政治攻防」?
更關鍵的是,這種語言策略並非偶發,而是逐漸成形的治理風格。近年來,從國會改革爭議、憲法法庭角色之爭,到預算與人事案的政治對抗,行政權越來越頻繁地以「民主正當性」或「憲法精神」作為抽象盾牌,卻刻意忽略具體條文與制度分工。短期看似有效,長期卻正在侵蝕台灣民主制度的信任感。
這種侵蝕,最終承擔成本的並不是政治菁英,而是普通民眾。對多數人民而言,憲法並不是抽象的法條,而是生活秩序的最後防線。當制度邊界變得模糊,政策不確定性提高,最先受影響的往往是依賴公共支出、社會福利與法治保障的弱勢群體。立法院預算審查若被動輒被亂貼上「違憲」標籤而草率通過,真正被犧牲的,可能正是那些需要被仔細檢視的支出項目。

從比較憲政的角度來看,成熟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通常會極力避免在憲法問題上使用過度簡化的政治語言。因為一旦開了這個口子,未來任何權力擴張,都可以被包裝成「憲法的另一種理解」。歷史經驗一再證明,憲政滑坡往往不是來自一次劇烈的破壞,而是來自無數次看似無傷大雅的詮釋偏移。
正因如此,這並不是單純的朝野口水戰,而是關於總統角色定位的根本問題。總統可以有其政策立場,可以爭取政治支持,但不應該成為「憲法的詮釋者」,更不應該在制度爭議中,既「當球員又當裁判」!否則,憲法不再是全民共同遵守的最高規範,而只是政治權力的附屬品。
長期而言,一個健康的民主體制,仰賴的是對制度不確定性的耐心,而不是對效率的迷戀。預算審查慢一點,憲政討論多一點,或許會讓政治看起來不那麼「順」,卻能讓制度走得更遠。相反地,若一再用政治話術壓縮制度空間,換來的只是短暫的行政便利,卻可能留下長期的憲政後遺症。
總統當然不是憲法的創作者!而只是憲法秩序下的產物。這個基本事實,不應該需要被反覆提醒。但當政治語言開始模糊這條界線時,社會就有責任重新把話說清楚。因為一旦憲法只剩下權力者的說法,那麼下一個被「重新詮釋」的,恐怕就不只是預算程序,而是整個民主制度本身。